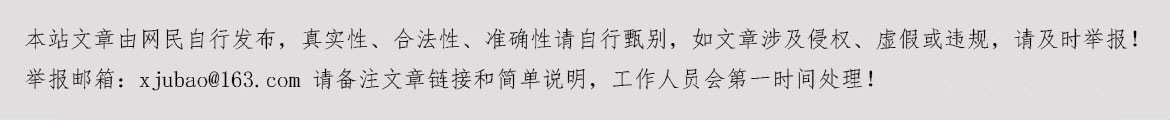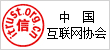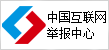滨城信息社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综艺娱乐、投资理财、教育科研、房产家居、生活百科、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封城期间 我谈了一段为期24天、只见过两次面的恋爱
2022-05-18 16:58:01
西安白癜风医院地址 https://yyk.99.com.cn/beilin2/105978/lianxi.html
作者 | 安心编辑 | 邱不苑
打开一个新文档,我敲下一行标题:《恋爱复盘》。这是一段为期24天、由于上海封城只见过两次面、却深深启发了我的恋爱事件。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这个套路得人心的社会里,
我们仍然相信,
唯有真诚最动人。
点它,纯净靠谱的交友平台XX。”
手机里弹出一则广告,我第一次对这种看上去不太靠谱的事情动了心。
我,27岁,刚裸辞,没有对象,一文不名,年初此起彼伏的疫情导致各处裁员,找工作更难了。或许先找个对象能改变我的运势呢?真是太衰了,总得做点什么改变一下局面吧,我下定了决心。打开app, 我注册了自己的账号,设定好筛选条件,在里面坚守了好几天,仔细阅读一封封推送来的简历。“长相中等,90年出生,身高180,在咨询公司工作,交大硕士,出身教师家庭,打算留在上海。”嗯,感觉很不错嘛,和我的情况非常相似呢,尤其是学历和教师家庭……这么想着,我点下了一个“喜欢”。
很快,我的“喜欢”就有了回应:“你好啊。看你的介绍在健身,很棒啊。”
“是啊,”我说,“虽然也是新手,但平时实在没什么事让我觉得自己还有在进步的了,只有增肌还能带给我一点成就感。”
不知道是不是对方感受到了我的丧,开始询问我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考虑到反正也是陌生人,我就敞开心扉和他聊了起来。
我说到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还有很多心结不能解开。在人生方向上也感到茫然,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心力交瘁,但又没有勇气去做自由职业者,光是想象外界的阻力都觉得害怕。男生那边很温和,帮我分析一项一项问题,朝好的方向引导对话,我们聊得十分愉快。
几天下来,我得知了我们都是非常细心认真的人,喜欢和平的沟通方式,思维方式都偏理性,老家都养了猫,运动后都超级爱出汗……
聊起学生时代,阿益和我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道路,高中的时候总考第一,但是又因为害怕失败心态变得很差,在无数个午夜的失眠中挣扎。我们也都在上了大学后面对新的生活内心一片茫然,学业上自甘堕落,遇到不合拍的恋人,但由于讨好型人格耗尽了自己全部力气,最终伤痕累累。我们仿佛心有灵犀,常常话还没有讲出口,对方已经了然,想举一个复杂的的例子,却发现根本不需解释……
他的形象在脑海中很快变得美好又亲切,仿佛多年未见的朋友。语音加视频沟通了三四天后,我们约定尽快线下见一面。3月底的上海正在推行动态清零,想要见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起床互相问候前,我们都要看看今天各自的小区封了吗,解封了吗,要不要做核酸?这一周周六的清早,突然间我发现小区门可以进出了,我激动地给阿益打电话,一小时后,我们进行了“战时突击会面”。
坐在整条街上唯一一家开门的饭店里,我们俩都有些局促,毕竟是第一次真正打量对方的全貌。阿益有着清瘦的身材,和照片上有些区别但似乎更好看些的脸,他穿着毛料西装和薄的高领毛衣,显得文质彬彬。比起略显成熟的穿着,他眼中不断闪现的喜悦和快乐让人想到一只胖松鼠,柜台后面的老板娘看着我俩笑意盈盈。
“那,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他问道。
“……这么突然吗?”我并没有想到他会单刀直入的向我表白,毕竟只是第一次见面。刚才得知能见面的第一时间,他下楼打了车往我这里来,而我连化妆的时间都没有,带着这几天日思夜想之余冒出来的几颗痘痘就出门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问出口了,”他讲话的时候喜欢晃动着身体,嘴角有着害羞的笑意,“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的。”
“那,行吧。”我说,用转来转去的眼珠掩饰着自己的不好意思。还好我们点的菜这时候上来了。
饭后在无人的街道散步,白色的樱花已经开了满树,只可惜今年的春天必然要错过了——疫情让整座城市风声鹤唳的。漫步经过等待做核酸的人们,我们牵着的手让队伍中正无聊的人们投来打量的目光。我发现他和我一样的内八,一样的怕冷,一样的手指甲盖形状,修剪的很短,我说:“你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他惊讶的看向我,果然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初见面后的我和他都陷入了深深的思念和焦虑中——手机上每天都冒出各种对疫情形势的消极判断和新闻。封城是大势所趋了。见面的三天后,我狠狠心收拾东西去了他家,既然要封,就封在一起吧!
阿益的家在市中心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里,他通过自如租了一个三室的单间,我去之前他和两位室友打好了招呼。他们平日里并无交集,但这样的举动让我觉得十分得体,又让我对这个彬彬有礼的男生产生了一些好感。
第一次进入他的房间,看到紧凑却整洁的陈设,我不禁想,果然和我想象中一样。他非常注重细节,衣柜里为数不多的衣物挂的整整齐齐,或是分门别类的放进抽屉,所有物品都一丝不苟的被收纳进有限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件物品像是多余的。目光又转到他书桌的架子上,啊,我和他的牙刷是同一个牌子诶,牙线也是同一款,也都买了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一瞬间我感到我们的共同点又增多了。
“比较简陋,委屈你了。”阿益帮我放好背包,转身回到电脑前工作。
这两天里,我开始了解阿益更多。他喜欢玩怀旧版魔兽世界,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只要有空就会去玩一会;他会拉二胡,平时也会一个人练琴,当得知我会弹琵琶之后他欣喜若狂;他每个周日的晚上都要和父母视频报平安,这一回也带上了我;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很像,都是高中老师的样子,温和中透着威严;他很擅长跑步,现在为了让我喜欢练起了肌肉。
在我们愉快相处的第二天晚餐后,阿益正在电脑上完成他这天最后一点的工作,我坐在一边玩手机,一切都自然而然。可忽然他生硬地抬起头,仿佛刚刚作出一个艰难又坚决的决定般对我说:“亲爱的,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你能好好护肤的话,我会尽全力支持的……”后面他又支支吾吾的说了很多关于皮肤养护的问题,他对医美看法的转变,还有他有个从事医美行业的表妹可以介绍给我认识等等。
一开始我有些不明所以,为什么他突然讲这些,虽然我平时常常懒得化妆,但我自认为皮肤是还不错的,只是时不时长几颗痘痘罢了,我的朋友们也都常表示羡慕我的皮肤白。后来看他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我又好笑又无所谓的说好好好,听你的,好好美白护肤可以了吧。阿益看起来很高兴,说:“宝贝需要什么护肤品,或者需要做水光针就跟我讲,我给你买。”
想着为了他开心,我开始上网挑面霜,最后选定一款在我看来很贵的产品,小心翼翼问男友:“你看这个可以吗?会不会太败家了?”在我为数不多的恋爱经验中,并没有什么花男生钱的经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阿益看了看价格,我心里十分忐忑,从后面搂着他的脖颈。他从电脑桌前转过来对我说:“从好的方面看,如果咱们在一起的话,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是应该的,从坏的方面看,如果我们分开了,至少你也不会觉得很亏。”
我大为震撼。我没有想到阿益会这么说,不仅没想到他会以这样冷静甚至冷漠的态度来分析这件事情,也没有想到他会以分手作为前提,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常常以分手为前提冷静的思考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他的父母因为认可我而欢欣雀跃的时候,他试图让他们降低期待;在我父母跟我了解男方家情况的时候,他让我好好听父母的建议不要擅自做决定和他在一起;在我结束了一场多愁善感的哭泣后,他常常说我不喜欢你哭,以后要改进不要哭了……
但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挺正常,甚至非常理解,因为严格的教师家庭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一颗敏感的内心——我也是容易过于谨慎以至于胆小的人。我非常理解他的谨小慎微,我们害怕犯错,不管是试卷上还是人生选择上。
和阿益在一起的这几天,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聊各自对未来的规划了。他很喜欢自己的咨询工作,对未来的发展也感到满意,不过他最常说的就是不喜欢太忙,不管是他还是我,都要开开心心地生活。因为我之前裸辞了,阿益建议我好好思考一下自己想做什么,不要像之前的工作一样不开心了。
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认真的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两年前毕业后,我像很多毕业生一样的迷茫,对步入社会这件事感到压力山大,稀里糊涂的工作了一年多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岗位后,发现自己偏内向的性格是胜任不了很多工作的,从一开始的拼命硬扛到后来的怀疑自己,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思考了两天后,我对阿益说,我想做一个编辑,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但如果从事自己所学,我会开心的。阿益对我表示了支持,不过同时,他也提出希望我做一个语文老师,因为教师家庭出身的我一定很会教书,也不会像某些行业一样辛苦。
当老师啊,我默默地想,并没有说反对的话。但其实我是稍微有些厌恶这个提议的,我开始觉得阿益和我在一起聊未来的时候,倾向于让我扮演一个他心目中设计好的角色,比如一个做老师、方便照顾孩子的母亲。我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是因为我的母亲,她一生操劳,因而不希望我也做老师,想要我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但看到畅想未来表情愉悦的男友,我没有说出来。
在他家的第四天,新闻传来:浦东被封了,四天之后就是浦西。没想到疫情真的走到了封城的地步,我赶紧回了家。
4月1日,阿益发来微信,是那只面霜的物流线路,从广东发到上海然后被自动退货了,我们还不知情的时候货物已经回到了老家。我哭笑不得,把那张截屏转发到朋友圈并配文:“上海市帮我婉拒了男朋友的第一份礼物(笑哭)”,底下不久就有了许多赞。这时候大家都还挺开心,以为隔离很快就会结束。
真爱的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在我身上,还多了一些不安。巨蟹座的我并不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社恐不自信还爱哭。十几岁还没有恋爱过的时候,我就怀疑过自己:将来要将自己的内心和别人坦诚相待,我做得到吗?
4月2日,隔离在家的第三个晚上,但有男友在手机那端陪着就一点也不无聊。阿益说他的发小们想看我的照片。我说好啊,我照片超级多的,正好也给你看看,说着就打开电脑给他发了一堆我从小到大的老照片。
突然他微信发来一条:“宝贝,你小时候超可爱的啊!”
原来是一张八九岁的我站在花丛中笑的照片,我有点骄傲的回复:“是吧,不愧是我哈哈。”
“不过,感觉你小时候有一种自信的神采,现在没有了。”
看到男朋友这样的回复,突然一阵苦涩涌上心头,我想起了过往那些因严格管教带来的窒息与压抑。在高考过去后的十年后我仍把它看作无意义的糟粕,因为自己一直都是被逼着努力,考第一的动机只是害怕、恐惧;而阿益虽然有和我类似的经历,却云淡风轻的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能做到就尽量去做啊。”他在微信里温柔的安慰我,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未来的时间足够你变成任何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了。
4月3日,也是我大姨妈前的一天,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不快让我钻起了牛角尖。我气恼阿益对我皮肤的苛刻要求,这让我十分有压力以至于没有安全感,我跟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而且觉得这种期待会让我感到自卑,和阿益吵了两句后他开始沉默。
4月4日,周围几栋楼里面陆续检测出了阳性,我们开始变得不敢开窗。白天我上网找了一位求职辅导的老师,沟通后,想要做一个图书编辑的规划在心中变得明朗,我终于有目标了!晚上我兴冲冲的跟阿益说了这件事,他为我感到高兴,然后问道:“不然再把针对老师岗位的简历一并修改润色好吧?”我说:“不,我想一件一件来。”阿益说:“如果求职辅导是按天收费的就一起做呗。”我说:“没事,我想抱着一定会成为图书编辑的信念去做。”
这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些隐隐的不悦。
“我只是不想浪费钱。”他说。
“没事不省这个钱。”我说。
“就是顺道的事吧。”
“可是我并不想当老师啊。”我的心情开始焦躁起来,觉得对方一点也不懂我,白天和求职导师连续沟通三小时后疲惫又无法停止转动的大脑在缺氧的环境中感到眩晕和灼热,我的呼吸开始困难:
“你不要干涉我了!你回去看看聊天记录,我拒绝了你6次,你就跟我爸妈一样,看不到我的意见吗?我也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请尊重我的意志!”
我的父母都是很粗线条的人,他们对我并不细心,尤其是小时候。妈妈还好些,这些年年纪大了,变得温和而怀旧,总能记得我上次回家时爱吃什么,还能念叨起我小时候的一些琐事。但爸爸永远是老样子,记不得我的喜好,还喜欢给我一些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我总觉得爸爸对我的爱只是因为他享受作为父亲的地位和掌控感。
自从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和父亲的矛盾就开始层出不穷。20岁出头的我好几年一直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要一直受到不合理的责骂。我远在国外,和家里经常用视频沟通,但几乎每一次和爸爸的对话都要以他战胜和我的辩论告终,我在精神上被欺压得痛哭流涕。
那时候的我还不理解父亲的不会放手,以及对苍老和无力的恐惧,就生生一次次吃下了他对我的语言暴力。想要出国的选择被责骂,一些对新闻的看法被嗤之以鼻,就连想要报个课外班学意大利语的决定都被骂得狗血淋头。逐渐的我开始不联系家人了,我开始习得性无助,以为和父亲的沟通一定会不欢而散,事实也是这样。
后来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让爸爸暑假来俄罗斯旅游。他很高兴,出发前发微信说:“最近的苹果可好了,一个要十块钱呢,又大又甜,我给你带两个。”
我的老家盛产苹果,但我不喜欢吃,自从懂事开始就拒绝吃,爸爸却怎么都记不住。我三番五次在微信上说不要给我买苹果我不爱吃,他却执意买了,一路背到俄罗斯,甚至罔顾我说的,海关不一定给你进来哦。在俄罗斯的两周里,他每天问我要不要吃苹果,我不胜其烦,但我明白这个60后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拒绝。
临走之前,我们一起去了机场附近一个很大的商场,逛了一圈后我们坐在餐饮区休息,爸爸又拿出他的苹果。他的眼神仿佛在拍一个广告,假想对面的我是克服了万般的引诱才努力拒绝了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你真的不尝一口吗?这是最后一个了,可好吃了。”他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种可能,别人对他喜欢的事物真的并不关心甚至厌恶。
最终在我的注视下,爸爸擦干这个宝贵的、历经了千山万水、每天被他背在身上的苹果上新鲜的水滴,一口一口的把它吃下去了。到今天为止,爸爸还是认为我会吃苹果的,或许是因为人总会遗忘他不想记住的东西吧。
阿益和我的微信对话,之所以让我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就是源于这些年来我的意见在父亲眼中的不被看见,不管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拒绝。他的心里好像有一堵墙,将我的一切意见阻挡在外,像一面镜子,将我的痛苦感受反射回自身。这种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感觉,逐渐的让我变得激动又无助。阿益本无恶意的劝说,在我看来,却像一只张牙舞爪像我扑来的巨兽,像一个要将我的自由锤入地狱的大锤,一锤,一锤的向我锤下来,而我要战胜它,战胜它,战胜它带给我的恐惧,我才有可能活下去。
和阿益结束聊天,我还不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理智,想必对方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触发了我的痛苦记忆。沉浸在自己是受害者的委屈中,我流着泪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和两女一男一起吃饭,其中一对是情侣,这位男生风评很差,不断做对不起女友的事,但朋友不听我们劝,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吃饭过程中我们和男生吵了起来,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三个女生激情谋杀了这位男性。事后我们都很害怕,心想摊上命案了。趁还没有败露,我跑去爸爸单位求助。想跟他说我要坐牢了,这件事很严重,要跟我去没人的地方说。可是爸爸一直在打电话谈工作表示让我在这直接说,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他我可能面临五年以上的徒刑。在梦中我一直思考着犯罪的后果,出狱后我会找不到工作处处遭到歧视,人生就此毁掉。可就算沉浸在无比真实的恐惧中,出庭前我问一同作案的女同学,后不后悔,她说,不后悔,我点点头,我也是。
后来我会想,这个梦已经解答了一切。我和阿益是真的想恋爱吗?我们双方认真的把恋爱这件事情放在人生中重要的议程上,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阿益不是一个渣男,我也不是一个渣女,我们从一开始对对方的筛选过程就非常审慎,希望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也尽可能的真诚。但这就足够吗?这样找到对方,结婚成家,就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吗?
父母那辈的人大多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梦魇中埋藏了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我们这一代无根的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却妄图依靠爱情这种最虚无缥缈的东西来获得自身的完整性。梦中的我想被理解,被看见,想挣脱这个世界上男权的控制,却在现实生活中妄图有一个男性来帮助我拯救我,让我不至于承担犯错的责任。
第二天早上醒来,阿益已经发来关心的信息,问我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对于昨晚突然的发作,我开始感到后悔而自责,后悔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我拨了电话过去。
电话对面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呆板,冷漠,而我非常困窘的说了些抱歉的话。阿益说:“丫头你有没有想过,你和我在一起,会从一个受控制的环境跳到另一个受控制的环境中去,对你来说处境并不会更好。还有就是,我之前就说过不喜欢你哭,你要学会让自己的情绪稳定。”
我的心有些发凉,一方面是因为对方又在审慎的用他的理性思维去考虑我们合不合适的问题,另一方面确实正如他说的,在他对各种细节的高标准前,我已经累了。有时我会想象,为了满足这个完美主义者脑海中幻想出的完美情侣形象,我要在工作之余做好身材和皮肤管理,保持微笑不随便发怒,不能想哭就哭,既要自我实现还要育儿顾家——这些都是他平日里在不断灌输给我的想法。
4月8日,封城还在继续,我囤的食物已经见底了,而我们这个默默无闻的社区还没有开始发放物资。半饿着肚子,我一遍一遍在文档里调整着面试需要的话术。下午,求职老师帮我做面试练习,问到我预期的薪资,我说:“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就行了,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可是在待业中。”
老师突然打断我:“小安你不能这么说,甚至不能这么想,这样把自己放的太低了。不管是对待工作还是对待他人,你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姿态放太低,一定要相信自己。”
我突然想到自己和阿益感情的开始,想到自己这半年来对找工作甚至对未来的恐惧,想到以前很多时候自己和恋人和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好像一切的症结都被这位素未谋面的求职老师点到了。
我太不自信了。阿益也是这样,我们都很不自信,过去的人生中总要面对更艰难的任务,总能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从小镇来到大城市,一直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却永远做得不够好。阿益曾在电话里和我说,自己非常怕遇到什么好事,比如彩票中大奖,他觉得这种事情会夺走自己其他方面的运气。有一天我们聊到以后买房的事情,我说妈妈同意出一半首付之后也帮我们还贷款,阿益像是很不舒服的皱起了眉头:“我们之后还是做好财产的公证,分得清楚一些比较好。”
想起小时候爸爸总安慰我说,性格不分好坏,但我觉得不全对,因为这些年来我的不自信给我带来的尽是些坏的影响。尤其是我很容易在低谷的时候寄希望于别人的拯救,我的恋爱好像都是在这种时候开始的,而男性们也常常被看上去弱小又无助的我吸引。结果就是,这些恋爱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男性的保护欲永远只是一时兴起的肥皂泡泡罢了。而阿益甚至没有办法产生这种保护欲,他和我一样的需要帮助,也和我一样的害怕失败。
4月9日,周围的楼栋拉走了很多例阳性,隔离在家的人们也陷入焦虑状态,有时候听到对面楼的人在阳台上大喊大叫,无聊的人们在小区群聊里也如脱缰的野马,聊得热火朝天。为了学习经验,我采访了三位认识的编辑,分别是童书编辑、当代文学编辑和原创文学编辑。
童书编辑是我大学时天天一起吃饭的好朋友,她安慰我不用焦虑,找工作非常看招聘者和面试者聊天的感觉,尤其是编辑岗位,要放轻松些;当代文学编辑是一位师兄,他非常谨慎的告诉我出版社之间区别非常大,岗位与岗位之间区别也非常大,尤其是有了多年工作经验后的他不敢给我一个可能是错误的期待;原创文学编辑是一位师兄推荐给我的女生,她告诉我不用因为之前没做过相关工作而不自信,中途转行反而可以看作是优势,因为做文学编辑是需要社会经验的,不然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和三位编辑聊过后,我的思路开阔了好多,好像自己之前的人生,就像这反反复复的疫情和隔离期,总是反反复复的被一些相似的阴霾笼罩,又反反复复的钻进自己给自己建造的逼仄的死胡同里,在窒息的空间里不断挤压自我,不断对周遭存在,对那该死的自我评判让步。
从小害怕被父母责备,就努力做一个好学生,长大了以后害怕被周围人落下,就努力在各方面向他人看齐,学校的排名、公司的待遇、穿着的选择,甚至自己的恋爱婚姻,都要在所有人认为的deadline前完成……这是不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媚俗”呢?我把自己的存在放在了最轻最轻的地方,尽管后来父亲总骂我固执,现在的男朋友也不觉得我是个听话的女孩,但还是太轻,太轻了,我把自己看扁了。
两天后,在视频聊天双方都和和气气的时候,阿益又提了分手。他是这么说的:“我想了很久,或许我太理性了并不明白什么是爱吧,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很有可能有一天我爱上你了,但是你已经太累了决心离开我了。”
对这次被分手我感到十分坦然,甚至早有心理准备——谁让我们心有灵犀呢。如果想通过说他的坏话表达不爽的话,我只想说:“你这个哈姆雷特式的懦夫,注定不会拥有爱情。”
回想起去阿益家的第一天,我在浴室看到一个粉色冲牙器,是阿益合租室友的,跟我一直用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我只想去相信我的男友和我拥有这么多共同点一定是命运的安排,却不愿意看到这只是因为我在一开始的社交app上开了筛选功能。后来的种种共通或者说“巧合”,也只能证明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是多么的普通、多么的不特别罢了。
我们被各种数据安排着一切生活,用相同的商品,想相同的问题,而之所以给对方赋予唯一的意义,只是想从爱情中寻找对自我的救赎罢了,但我们显然不是对方的解药。
4月的最后一周,上海人仍然被封控在家里,我开始习惯每天做一次核酸的日子。和阿益的联系已经断了很多天了,分手之后我们仍旧默契的没有互相打扰。找工作的事有些眉目了,面试邀约断断续续的来了,我也花了一番功夫将这段早夭的恋爱故事落在了纸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或是机关算尽,也没有缠绵悱恻后的午夜梦回。我们就是这么普通,普通到都对自己不自信,普通到没有勇气克服困难一起走下去,就在网络上断了联。恋爱24天,只见过两次面的我们又一次成了陌生人。
我仍能回想起阿益畅谈他梦想中的模范情侣,他的眼神里有光。
咬一口刚团到的大番茄,我感到轻松极了。哪怕我的生活与这座城市一起停滞不前,哪怕以后还会踏入种种以爱为名的陷阱,此刻我只想好好感受这一口沁人心脾的清甜。